民国的天空是灰色的,战火纷飞,山河动荡,人心浮动。可偏偏在这样的年代,一群读书人却把烟火气熬成了诗,将粗茶淡饭品出了禅意。他们不谈流量,不求点赞,只在一碗炸酱面里寻找北平的旧影,在一枚咸鸭蛋中打捞故乡的月光——不是他们所在的年代好,而是他们把日子,活成了好味道。
梁实秋:雅舍谈吃,吃得有文气
梁实秋是民国文人中最著名的“吃货”。他一生写下《雅舍谈吃》百余篇,字里行间皆是舌尖上的乡愁与生活的智慧。
他出生在旧北京,自小迷恋和钟情于京都的饮食文化,对菜肴食品的品质、季节性以及烹饪的分寸感都很重视和考究。哪怕是一碗炸酱面,也要讲究:面一定是抻的,酱炸到八成之后加茄子丁,四色面码:掐菜、黄瓜丝、萝卜缨、芹菜,一样也不得少。他还曾在文章中详细记叙了“菜包”的配料及其做法,并标明其由来乃是原清朝王室每年初冬为纪念其祖先作战绝粮吃树叶而发明出来的。
在青岛任教时,梁实秋租房于鱼山路,常在清晨踱步至附近的海鲜市场,挑选最新鲜的海产。他在《忆青岛》中写道:青岛的海鲜齐备,像蚶、蛤、牡蛎、虾、蟹以及各种鱼类应有尽有。在大雅沟菜市场,他花六块钱买到了一条鲥鱼,二尺半还多长,嘴巴小、鳞片细,看着就像刚从海里捞上来的。带回家切成几段,全家吃了好几顿,那味道鲜美的程度,真是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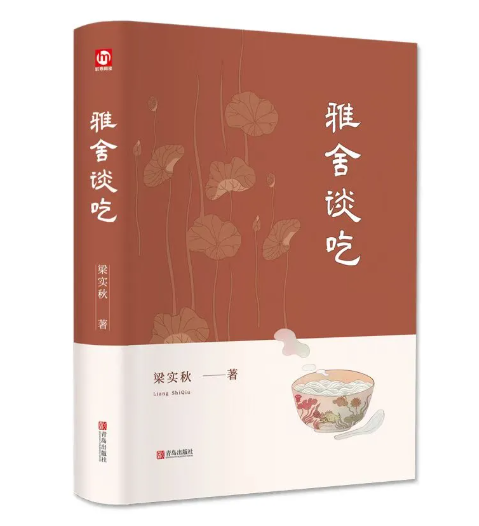
他在《雅舍小品》中写道:“馋非罪,反而是胃口好、健康的现象,比食而不知其味要好得多。”这话轻描淡写,却藏着一个文人在乱世中对生活的庄严态度:再苦的日子,也要认真对待一箪食一瓢饮。
汪曾祺:家常菜里的诗意江湖
汪曾祺的吃,是“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他的笔下,最动人的不是山珍海味,而是家乡的高邮咸鸭蛋和大煮干丝。
“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这“吱”字,是汉语饮食文学千年才炼出的一个拟声词,脆生生的,刚好透着红油的鲜灵劲儿,看着就勾人食欲。他曾写道:“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

汪曾祺的儿子汪朗回忆父亲:“按厨师排位他是排第一把手。家里做饭,几十年都是他管的。做的最多的,就是他老家的那个大煮干丝。”汪曾祺对干丝的喜爱,体现在很多文章中。他写干丝:一种特制的豆腐干,较大而方,用薄刃快刀片成薄片,再切为细丝,这便是干丝。讲究一块豆腐干要片十六片,切丝细如马尾,一根不断。煮干丝要用小虾米吊汤,下火腿丝、鸡丝,煮至入味,即可上桌。
在北京没有适合切干丝的豆腐干,他就用高碑店豆腐片替代,选那种片薄又有嚼劲的,切得细细的,跟扬州的方形豆腐干一样。这道菜成为了他偶设家宴的保留节目。
“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汪曾祺的食事散文,核心从来不是 “物”,而是 “ 人”。他强调做饭最大的乐趣还是看家人或客人吃得高兴,他说:“愿意做菜给别人吃的人是比较不自私的。”
这其中体现的“人情”,正是今日算法喂养的美食博主最缺的滋味。
鲁迅:冷笔写世相,甜口慰平生
世人皆知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却不知他书案一角常年摆着糖。
1926年,鲁迅的学生从河南给他带来两包方糖,用柿霜制成,本用来治口腔溃疡。这糖吃起来又凉又细腻,他一口气吃了一大半。到了晚上,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琢磨着,毕竟嘴角生疮的情况不会多,不如趁新鲜再吃一点,于是爬起来找出藏着的糖,又吃了一大半。

鲁迅不仅爱糖,还爱一切甜食,即便饱受牙疼困扰,也不愿意忌口。他吃过的甜食和点心有:桂花白糖伦教糕、蜜饯、萨其马、奶油蛋糕、柠檬糖、羊羹、三不沾、京八件、猪油白糖莲心粥……他称自己“只要胃口好,可以从早晨直吃到半夜 ”。
鲁迅吃的甜,是苦中作乐。他在《两地书》中写道:“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做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或者就是糖罢。”他的文字如刀,可心底始终藏着一块化不开的糖:冷眼观世,热肠待人,甜味慰心。
郁达夫:酒肉才子,吃得深情
“大醉三千日,微醺又十年”。郁达夫一生嗜酒好肉,饮食极富个人色彩。他的好友郑伯奇在《回忆创造社》一文中记录郁达夫:“哪一家的美酒味醇,哪一家有什么可口的下酒菜,他都一一介绍,如数家珍。为了品味,有时我们会连续吃上几家酒馆,他常常喝得面带微醺,更加意气风发,滔滔不绝。”
1927年定居上海后,郁达夫常与友人出入南翔小笼、老正兴、德兴馆等本帮名店,尤爱蟹粉狮子头、㸆鳝、醉鸡等菜式。后在福州任职,他对街头小吃情有独钟,尤爱鱼丸、蛎饼与鼎边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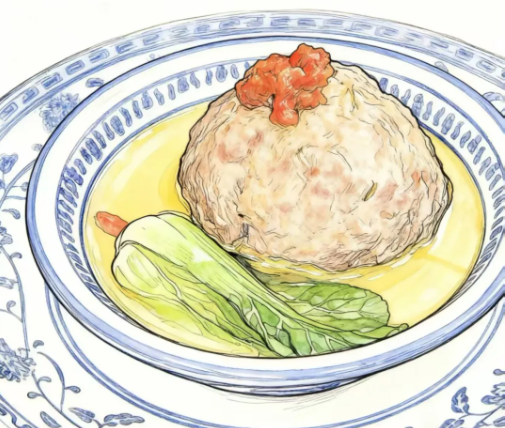
他在《闽游滴沥》中写道:“鼎边糊味极清鲜”,还曾在蚌肉上市季连吃数百个,自认是 “此生的豪举”。一碗朴素的风味小吃,在他眼中,已是乱世中难得的人间慰藉。
郁达夫的餐桌,从不只为果腹。他常自掏腰包请穷学生吃饭,席间谈文学、论国事,酒至半酣,往往拍案而起,慷慨激昂。他的饮食,是文人的豪放,也是寒夜中的薪火。
张大千:画坛巨匠,厨中圣手
“一个不懂得品尝美食的人怎么可能懂艺术”,张大千一生云游四海,遍尝各地美食,他广采诸味精华,在自己的烹饪中巧妙吸收,并加以创新,研制出各种美味菜肴来。无数文人雅士、政界要员、门生亲朋,都曾是他的座上客。每次家中开宴,他便亲书食单,交给私厨置席,还时不时亲自下厨。他曾自豪地说:“以艺事而论,我善烹调更在画艺之上。”

张大千宴客极尽奢华却不失雅致。一道“干烧鳇翅”需提前三日准备,一条“六一丝”(六种蔬菜加火腿丝)要刀工如发,一道“大千鸡”必须用刚生出鸡冠的小公鸡……凡是被张大千宴请过的宾客无不称赞。其中,以吃客著称的林语堂曾对人说:“我这辈子吃过最好的宴席是在张大千家里。”
一个绘画大师,深入厨房,将食事当作了艺事。他用一生证明:真正的艺术,既能落笔成山河,亦能下厨调百味。
民国文人的“吃”,究竟比今日美食博主强在哪里?
一在慢,二在真,三在情。
梁实秋为一碗正宗炸酱面较真北平酱园的甜酱;汪曾祺为一碟家乡咸鸭蛋直言“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鲁迅为一块柿霜糖半夜起身,不顾 “牙疼如故”悄悄吃光大半罐——他们不赶流量,不怕掉粉,只是心之所向一餐烟火真味。

而今日的美食博主,在算法指挥棒下,迷失了方向,弄丢了本心:
其一,重形式轻本质。镜头对准摆盘,却看不见食材的灵魂;滤镜调出食欲,却调不出岁月的滋味。一碟青菜,P图后光鲜亮丽,可谁还记得菜叶上露珠的重量?
其二,追热点弃传承。今日复刻宫廷菜,明日挑战黑暗料理,却无人静心学做一碗真正手擀面。流量如潮,来去匆匆,留下满桌狼藉与空洞的胃。
其三,求速成失匠心。五分钟教会米其林,三天打通厨艺关——当“快”成为唯一标准,食物便失去了等待的庄严,烹饪沦为了表演的道具。
我们拥有比民国更丰富的食材、更先进的厨具、更便捷的物流,却在信息洪流中,弄丢了最珍贵的东西:对食物的敬畏,对时间的耐心,对生活的诚意。
或许,是时候关掉手机,洗净双手,认真煮一碗饭了。不为点赞,不为带货,只为让食物,回归食物;让人,回到人。
